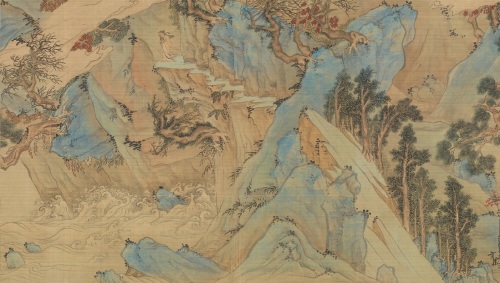
倘若有眼病,会影响视觉,致使要画辽阔的山水画时亦难如愿。像莫内就因为白内障,而导致他绘画时会绘出轮廓不清、色泽混浊的图画。(图片来源:台湾故宫博物院)
白内障早期的症状有视力模糊、色调改变、怕光、眼前有黑点、复视等,晚期症状则为视力障碍日深,最后只能在眼前辨别手指数目或仅剩下光感觉。
视力影响莫内的着色能力
由此可见,晚年患有白内障的莫内,其创作、生活是何等艰辛。色彩的运用奠基于画家对色彩的认知。莫内的用色从亮丽到阴暗的变化,正源于他眼中看到的颜色已经起了变化,这种变化在他晚年创作的《睡莲》等画作上可得到切实的证明:不仅色调,甚至亮度也显得浑浊而阴暗;此外,因为对比感减弱,描绘的形体、轮廓全部显得含糊不清。朋友们回忆说,当时的莫内只看得到白色和绿色,蓝色已经变暗或变成紫色,早期作品中那种光感和氛围感已不见踪影。换言之,莫内画作里出现的模糊、黯淡,很可能正是他“忠实记录”着自身所见景象的结果。
可见,视力影响了莫内对色彩的运用,从而改变了艺术效果,有可能在无意中形成了印象派风格。
征服顽疾 长路漫漫
白内障当然不是新出现的顽疾,人类早就深受此疾困扰,在历史长河中一直试图征服它。
不同于许多疾病的治疗长期与药物纠缠,人类很早就关注到用手术的方式解决白内障。
苏胥如塔最擅长白内障手术
据说,白内障手术的最早纪录出自《圣经》和古印度史料。西元前七世纪,古印度出了一位类似中国扁鹊和华佗般的神医--苏胥如塔(Sushruta),他的拿手好戏就是白内障手术,当时即闻名遐迩。为了顺利完成手术,苏胥如塔在经验的积累之上,创制了一款叫作Jabamukhi Salaka的特殊工具,专用于白内障手术,这是一种用来松开晶状体并将其推走、移动的弯形针。
据史料记载,苏胥如塔为病患实施手术之后,病眼要先用温热的黄油浸泡,然后再扎上绷带。虽然这种方法在一些病患身上取得了成功,但苏胥如塔警告,白内障手术只有在绝对需要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至于他指的“手术绝对适应症”(indication)到底是什么,和现代的有何差别,则是医疗史专家深感兴趣的话题。
另一方面,苏胥如塔的开创性手术也为后世治疗白内障开启了思路大门。
原来,根据晶状体的变化,白内障一般可以分成初发期、膨胀期、成熟期、过熟期四个阶段。
如果成熟期持续时间过长,经数年后,晶状体水分会继续丢失,体积缩小,囊膜皱缩,出现不规则的白色斑点及胆固醇结晶。晶状体纤维则会继续分解液化,呈乳白色甚至棕黄色,此时的晶状体核会沉于囊袋下方,甚至可随体位变化而移动。当晶状体核下沉后,原先被浑浊的晶状体阻挡的光线就能进入眼内,病患视力将突然提高,貌似不治而愈,实际上眼睛的风险愈来愈大,因为那些自然掉落在眼球其他位置的晶状体会被免疫系统攻击,诱发炎症和青光眼,后果极可能导致失明。
古人很早就观察到这种病患眼球的反常现象,显然也从中得到了启发。苏胥如塔的白内障手术原理,就是以人为方式让病变的晶状体脱离其原有位置,避免遮光,改善病患的视力。
古籍记载白内障手术
有人会问,相机的镜头被取走了,还能拍照吗?其实,人体器官的构造远比相机复杂,而且更有灵活性、适应性。浑浊的晶状体被移动或剔去,反倒能让光线顺利抵达视网膜,只是没有了晶状体屈光调节的作用,病患相当于被人为改造成一千九百度左右的远视,但总比白内障时的视力好些,毕竟远视可以透过戴眼镜矫正。
以治疗白内障为例,古印度的眼科学已十分先进。与西域交通频繁的唐代(甚至更早的时候),印度眼科学便已随着佛经传入了中土。有趣的是,唐朝人患眼疾,求助于印度(天竺)医学似乎十分普遍,其中就有“金针拨障术”,又名“金篦”术,这是中国古代医学家研习印度眼科学之后,针对白内障施行的一项改良手术。
从古籍的记载来看,白内障患者接受这项手术后,一般都能改善症状,成功率达六○%左右。
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对此均有记载,民间享有盛誉。唐代有些诗人在作品中曾多次提到“金篦”术,如杜甫的〈秋月夔府咏怀〉有“金篦空刮眼,镜像未离铨”,以及〈谒文公上方〉的“金篦刮眼膜,价重百车渠”。李商隐的〈和孙朴蟾孔雀咏〉也有两句“约眉怜翠羽,刮目想金篦”。
享年五十八岁的杜甫体弱多病,中年后患有糖尿病,晶状体有毛病不难理解,尽管常常饥寒交迫,但还是有可能接受过白内障手术,诗作估计是他的真实体会。至于李商隐,享年仅四十五岁,他是否得过白内障并有亲身治疗的体会,目前存疑。

杜甫有可能接受过白内障手术,〈秋月夔府咏怀〉等诗作估计是他的真实体会。(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金针拨障
“金针拨障”就是用特制的针将晶体周围的悬韧带拨断,造成晶体的脱位,使游离的晶体下沉到眼部玻璃体腔内,让光线不被阻挡。不过,站在今天的科学角度看,金针拨障只能暂时解决部分问题,无法彻底治疗视力障碍,而且由于晶状体残留在异位,眼内炎症反应时有发生,反而在日后更加损害病患的视力。
欧洲的白内障手术史
欧洲人对白内障及其手术的认识较印度和中国晚很多,但在文艺复兴之后急起直追,对于眼睛细微解剖结构的认识,已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1753年,法国医生戴维尔(Jacques Daviel)完成了世界上第一台传统白内障囊外摘除术,标志着古代白内障手术的终结,人类已进入近代白内障手术时期--将浑浊的晶状体取走,不再让它残留在眼睛内。
不过,欧洲人的手术刚开始时其实比较粗糙,伤口过大,创伤过深,又没有麻醉药的支持,更缺乏无菌观念,有的医师甚至直接用手指把晶状体挤压出来,使得手术的并发症非常严重。莫内开刀时,白内障手术已较前期进步,但仍有缺陷,因为人们还没发明可以替代原有晶状体的物体,亦未开始应用消灭病菌的抗生素;于是,病眼的感染导致出现新问题,伤口因此愈合不佳,对视力仍旧构成威胁。
有志者依旧走在探索的道路上。
二战期间,英国医师哈洛・瑞德利注意到飞机挡风玻璃异物虽然长期残留于飞行员受伤的眼睛里,却能保持稳定,异物对周围组织的刺激不明显,由此受到启发,发明了人工晶状体。
1949年,他将首枚玻璃人工晶状体植入病患眼内,开创了白内障手术的新纪元。可惜当时莫内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从那时至今,尽管材料和器械早已更新换代,白内障手术的基本原理没有再发生大的改变。
莫内一生画笔未停,简直就是绘画界的文学巨匠巴尔札克,但他的第二任妻子在1911年不幸去世,长子于1914年亡故,这些沉重的打击都严重加剧了莫内眼部的顽疾。尽管如此,他的画笔从未放下,只是笔下的莲花愈画愈大。莫非这同样是眼病造成的影响?去世前三年,莫内忍不住煎熬,接受了白内障手术,据说术后他看到了常人难以觉察的紫色,便把这种感受带到创作中,甚至重新绘制了部分作品,睡莲的颜色更深了。
(本文节录自时报出版、谭健锹 著作的《世界史闻不出的药水味:那些外国名人的生老病死》一书)
